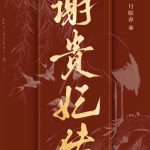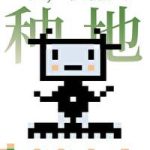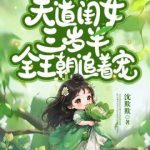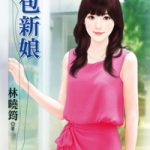第 101 章 外傳:他在江湖裏,溫潤如玉(一)
外傳:他在江湖裏,溫潤如玉(一)
有一奇山位于大秦國境極北之地,因大霧終年彌漫,山體常常隐藏于濃霧之中使常人不得見,因而得其名—霧隐。霧隐山相較其它名山沒有那麽多有名的山峰,只有大小兩座叫得出名字的山頭,大的是主峰也叫做霧隐,是為霧隐峰,小的叫做北陰峰。
兩座山峰中間有一鐵索橋,這橋年頭久遠,通體只有四根鎖鏈,綿延二百來米,上面木板早已破破爛爛。這鐵索橋就連霧隐峰上最老的老人都不知道是何人在何時所建,極其神秘。
這橋也只有在北陰山霧隐觀讀書修行的張先生在給霧隐峰幾十個孩子上課時才會走上一趟。村裏的人都勸張道長幹脆在霧隐峰上再建一座霧隐觀,既省去道長來回走吊橋的危險路程,再者說,霧隐峰上霧隐觀,比北陰峰霧隐觀順耳多了嘛。但是張道長總是委婉回絕,說什麽“鐵索橋經年不毀,若是貧道走上幾遭便損毀,豈不成了破壞古跡的罪人。何況貧道乃讀書修行之人,若心境不穩,猶生恐懼,如何做得了孩子們的教書先生”。
張道長是十年前突然出現在霧隐峰上的,當年霧隐峰上的村民見到他從北陰山那條鐵索橋上緩緩走過來時,都大吃一驚,以為是天上神仙。當時張道長一襲麻布青衫長袍,頭發用木簪子盤起來,面白須淨,眉宇間有春意盎然。村民們都熱情好客,也都好奇這個英俊青年的來歷身份,都争相邀請這個文靜的青年人去家裏做客,張道長也都不拒絕,一家一家赴約,足足逗留了半月有餘。
村民們聽村裏的王老秀才說,張道長的學問比他還要大上幾百倍。村長便把大家叫到一起合計着,王老秀才年歲已大,教這幾十個孩子已是力不從心,不如将那張道長請來做孩子們的教書先生,或許村裏還能出幾個秀才呢。于是,張道長每三天便從北陰山的霧隐觀經鐵索橋來到霧隐村給孩子們上課講學。每次逗留時間都不一樣,可能是半天,也可能是半個月。
張道長每次來村裏講學,吃飯、住宿都是在那兩間茅草屋學堂裏面,先前便已講好,張道長在村子講課期間,村子只需準備食材即可,生火做飯,他自己來。有哪家孩子生病沒來聽講,張先生便會在一張比天上的雲還白的紙上,寫下今日講課的要點,親自送到孩子手裏。先生的字,用王老秀才的話來說,就是翩若驚鴻、矯若游龍,有仙人氣象。那群孩子不懂,只是覺得這紙好,拿在手裏涼絲絲的舒服;這字好,比村裏最好看的姑娘還要好看;當然,還是先生的人最好。所以有的孩子為了得到張先生的親筆墨寶,竟然想出來裝病這個法子。先生看出端倪後,便笑着給每個孩子都寫了一張紙。
王老秀才在張先生講課的時候,也端坐在下面,像學生一樣,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張先生每次來村裏,王老秀才的嘴巴都能咧到耳朵後面。因為只有在張先生來的時候,他的老伴才會準許他在村裏唯一的小鋪子那裏打上二兩散酒,用他老伴的話說,你與張先生喝酒時,最像當年讀書求學時的模樣。學生放學離開學堂後,差不多已是黃昏了,這個時候,孩子們都能看到,他們的王老先生佝偻着身子,笑呵呵地走近裏屋,把準備好的二兩散酒拿出來,與張道長小酌兩杯。
村長先生很少來找張道長,但道長每次來學堂要準備的食材、用度,都是村長親力親為。王老秀才喝酒不過瘾時,總喜歡拍拍村長家的門,說道長喝酒沒盡興,還想嘗嘗村長院子裏十年前埋下的桂花釀。村長也不開門,只在裏屋說,給你家小淵考上秀才,哦不,考上舉人時留着呢。王老秀才一聽這話,丢下一句,你等着吧,便滿心都是歡喜得意地離去了。村長在感謝道長答應為村子裏孩童們講學時,開過一壇,王老秀才說那香味都能把你女兒引來了。這桂花釀,本來是等村長家的姑娘出嫁時用的,沒想到姑娘到縣裏面讀書,被游學至此的一位士子拐走了。只寄了一封書信,說是嫁到了郡裏面。後來姑娘也帶着女婿回來過一次,看上去沒受委屈,只是他們只住了一晚便走了,酒席都還沒辦。後來,村長老夫妻倆也就請親戚們吃了一頓,便草草了事。
王老秀才在與張先生喝酒的時候,從來不問張先生師承和其他人情世故,只知道談論一些春秋亂世,安邦定國的大事,說年輕時讀書想要治國平天下的志向、說那帝王心術伴君如伴虎。大多時候都是張先生在聽,王老秀才人雖幹瘦,但肚子裏的墨水可真不少,有時候已是月上梢頭,酒壺空空還覺得不盡興。
張道長講學沒有書本,孩子們在他的課上只管聽和問,不要求做筆記,連練字這項讀書人必修的課業都只是自願。王老秀才解釋說,這是因材施教。村民們不懂,但是看着自家孩子越來越懂事,有時還會念叨幾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也就由衷佩服那位張道長。
就這樣平靜度過五、六年時光,那時候,村裏面竟然又有人考中了秀才,甚至王老秀才的兒子應村長的預料還中了鄉裏的舉人。當郵差氣喘籲籲送達喜報的時候,王老秀才高興地手足無措,都忘了請郵差進屋喝杯茶水,還是王老秀才的老伴趕忙給郵差倒上茶水,又要張羅着做飯。郵差只喝了杯茶水,又給水囊裝滿水,就告辭了,一句山路崎岖的怨言都沒有。送走郵差後,王老秀才趕忙拉着給自己漲了臉面的兒子王淵去給祖宗牌位上香,以求祖宗天上有靈,讓他們王家又朝一日能走出這霧隐山,去縣裏甚至郡裏為朝廷效力。
為了兒子前途去向,王老秀才與張道長喝起了悶酒。
這小子一點當年我求學時的雄心壯志都沒有,真是愧為讀書人,空要那一身學問有什麽用
老哥,修身、齊家、為往聖繼絕學,王淵這孩子,志向已經很遠大了。
說到底,道長還是道門中人,不理解我儒家子弟入世治世的心情啊。
人各有志,強扭的瓜不甜,老哥又何必煩心,孩子長大了,就由他去呗。
張道長知道,王老秀才是不想浪費了王淵的大好前程,20歲第一次中舉,這在整個大秦龍尾郡都算上等讀書苗子了。他不想自己的兒子步自己的後塵,在村裏教書固然不錯,但是這種安逸的環境會讓人慢慢地忘記了自己的初心,他怕兒子一輩子也只是普通的教書先生,做不來那立言之人。但世事無絕對,自己不後悔就行,就像王老秀才,現在看着村裏面是個認字的人見了他都得彎腰叫聲王先生,他就覺得,這輩子值了。
張道長有一回下山,過了一個月才回來。幸好王老秀才的兒子王淵留在村子,頂了張道長的缺,不然一個月時間,夠這幫野孩子忘掉大半所學了。
張道長回來的時候,牽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道長說,是親戚家的孩子,托他照顧幾年。以後跟村裏的孩子們一起上學,帶過來認認臉。村裏人都覺得孩子長得那叫一個标志,粉雕玉琢的小臉像是個瓷娃娃,看起來就像是大戶人家細心養護的孩子,衣服飾物好看得很,跟人一樣。聽村裏最見過世面的村長說,這孩子一身衣服飾物都能買下整個霧隐村了,村民們一陣唏噓。孩子剛到新地方,有些怕生,躲在張道長身後,不敢與人說話。
少年叫做權七,跟張道長一起過鐵索橋,跟村子裏的孩童們一起聽道長講學,吃喝皆是山裏的粗茶淡飯。在北陰山霧隐觀裏,他每日清晨都要起個大早跟道長去山腰一處泉眼挑水,挑滿一缸為止。小孩子力氣小,拿起木桶都費力,道長便給他做了一只小木桶,道長用大木桶、大水缸,小七用小木桶、小水缸。道長說,沒有人能一輩子照顧你,你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
小七每天一大早挑的清澈山泉有一半用來沖涼,道長說,冬天也要如此,對身體好。挑完水,小七還要劈柴、生火,道長要教他燒飯,道長說,民以食為天,吃飯、睡覺是最重要的事。吃過早飯,已是八點左右了,道長會帶着小七一起念道經“道可道,非常道”,道長說,書讀百遍,其義自見。
小七很喜歡霧隐山上的學堂,因為在那裏,他不用挑水劈柴了,但還要早些起來念書。學堂裏有些和他年歲差不多的孩子個個都會燒火做飯,聽說還有人會播撒麥子,俨然已是小小莊家手。小七很佩服這些人,所以也想跟道長學習播撒麥子,他說,他不想被別人瞧不起,父親告訴過他,不要讓道長對他失望。
道長果真就帶着他,在學堂旁邊開墾出一小塊田地,從除草、撿石、翻土到播撒麥種、施肥、澆水,忙活一整天,一大一小兩人終于開墾出一小塊麥田。小七很累,但是很開心。他不僅會播撒麥種,還會開墾荒地了呢,在這裏他不比別人差,和從前一樣。
學堂裏聽課的小孩或者年輕人都叫道長先生,只有小七叫道長陵叔。剛開始的時候,小七還不習慣這裏的孩子們,因為實在是太野了,而且還都是他不會的玩意。上樹掏鳥窩,溪邊捉魚、洗澡,泥漿裏打滾也能玩得不亦樂乎,他覺得不雅,有些不好意思。直到道長對他說,在這裏,你和村裏的孩子一樣,去玩吧。得到首肯,放開來玩之後,他才發現,原來在鳥窩裏嗷嗷待哺的小鳥是那麽可愛,鳥蛋煮熟了沾點辣椒比雞蛋要好吃,在泥漿裏滾過後,即使用水洗過也還是覺得身上不舒服。一個月下來,小七剛剛進村時白嫩嫩的皮膚便黝黑許多,但是也變成了掏鳥摸魚的好手,在孩子中間很受歡迎。
小七還是跟以前在家一樣,每天練半個時辰的字,先生知道後,便讓他抄寫道經。村裏其他孩子都很喜歡的白色宣紙,小七有厚厚的一沓。小七的字寫得很官方,方方正正,是大秦的正楷體。有些同學豔羨小七的字,跟先生說一聲,便也得到了一些宣紙,不過先生說必須得寫完,于是每天傍晚和小七一起練字的人越來越少。不過有一個年輕的教書先生每天都和他一起練字,這位村子裏其他人尊稱的小王先生對他極好。每當老王頭來找陵叔喝酒時,都是小王先生陪他玩,老王頭在那裏跟陵叔談論天下,小王先生就和他說小溪邊那個地方魚多一點,什麽時候捉魚更容易。有幾次被老王頭聽見小王先生跟他說這些,氣得老王頭的胡子都豎起來了,小王先生笑着跑開,還說下次再跟你說說那掏鳥之道。老王頭雖然兇,但是小七也是很喜歡他的,因為從小七來村子後,他每次找陵叔喝酒時,都會帶些吃食來,一把炒熟的花生米,幾塊自家腌制的柿子餅。有時候老王頭還把村長叫來,他就能吃到更高級一些吃食,過着面糊炸得兩面金黃的小魚,村長從縣裏面帶回來的糖人,雖然每次都化成糖水了,他也覺得甜。
小七喜歡霧隐峰上的學堂,但他實在害怕那鐵索橋。道長走在前面,穩如泰山,他走在後面,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直到後來,權七才明白,如果他不慎掉入深淵,道法通天的陵叔可以一瞬之間救起他。後來,陵叔笑着告訴他,那條鐵索橋是為了看你心性,看你是否勇敢走上去,看你是否能穩住,原本對你的期望也就是走兩三步便要吓得難以動彈了,誰知道你啊,一口氣走完全程了,這份心性,很不錯。